血衣镇
2020年4月1日21:40:36
原作家:庄秦
http://www.99csw.com/book/7957/275765.htm
第一章
走了一整天的山路,临近傍晚的时候,我与陈璞终于登上山脊,向下望去,看到了笼罩在一片紫色雾气中的血衣镇。
小镇破旧不堪,房屋歪歪倒倒,人烟寂寥,再加上远处不时传来几声乌鸦悲恸的啼叫声,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某部哥特式恐怖小说中的场景。
小镇外的山坡上,有几座稀稀拉拉的坟茔,没有墓碑,只有一堆腐朽的陈土,插着歪歪斜斜的十字架。
当山风掠过的时候,无数白色的细碎纸屑迎风飘舞,那是祭拜先人的纸钱。
看着漫天飞舞的纸钱,陈璞忽然在我耳边幽幽地说:“唉,三天后,这里又会多上两座墓了。”
陈璞是我读大学时的好哥们,三十岁,与我同龄。
三天前,他打电话给我,让我陪他一起回一趟家乡——血衣镇。
因为,他的父亲与母亲在一周前,同时离开了人世。
陈璞的父亲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,因为一场久未治愈的肺痨病,终于撒手人寰。
在他断气的同一天,与他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,在一幢古老而又阴森的老宅里,用一根结实的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尾随丈夫一起去了遥远的天堂。
当我和陈璞搭乘远郊班车前来血衣镇的时候,他就无数次在我耳边念叨:“唉,王东啊,我早就让他们到城里来享享清福,可他们就是舍不得家里的老宅,不愿意离开。
哪怕生了病,也不肯到城里来看医生。
没想到……”说着说着,他的眼眶里就盈出了一汪泪水。
作为陈璞最好的朋友,在这个时候,我也只能安慰他:“别伤心了,老年人都是念旧的,也是最重感情的……”
在默然之中,我们沿着逶迤的山路,走下了山脊,来到血衣镇的镇口。
天已经暗了下来,紫色的薄雾中,我依稀辨出,在镇口外,有一条小河,一座木桥架在小河上。
已经是初秋了,河水并不湍急,无声地流淌着。
为了岔开话题,我问陈璞:“为什么你的家乡要叫血衣镇?这真是个诡异的名字啊。”
陈璞答道:“传说在很多年前,这里发生了一场很残酷的战争。
嗜血的胜利一方将几千名战败俘虏带到了河边,残忍地砍掉他们的头颅,将无头的尸体扔进了河中。
死者的鲜血,淌在河水之中,又渗进河边的沙滩上。
所以,整条河的河水都被染成鲜红色,至今,河水依然是红的。
镇里的人用河水浆洗衣裳,所有的衣物也被染成了红色的,就如血衣一般。
所以,这个小镇一直叫血衣镇。”
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。
我走上木桥,倚着木质的栏杆向下望了一眼,河水缓慢流淌着,河道散发出腐烂的血腥气味,令人作呕。
昏暗的夕阳下,河水的颜色很深,像一团死人毛发酿成的酱油。
果然,河水是红的。
难怪连这里的雾,都是紫色的。
蜿蜒河道的上游,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传来了“砰砰砰砰”的声音,节奏很慢,是谁在用木棍敲击着河边的卵石。
陈璞说:“那是镇里的妇人,正在用河水浆洗着衣裳呢。”
第二章
刚走进小镇,我就看到几个穿着红色衣裳的小孩,正在铺着青石板的道路上,玩着纸牌的游戏。
他们听到脚步声后,缓慢停下了手中的游戏,抬起头来望向我和陈璞,眼中流露出奇怪的神情,那是一种很呆滞的眼神,他们的瞳孔前,仿佛笼罩了一层雾,看似没有一点感情,却又都死死盯着我们。
正当我觉得有点纳闷的时候,其中一个孩子忽然跳了起来,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,重重向我们砸来。
猝不及防之下,石头砸在了陈璞的手臂上,让他发出了一声呻吟。
我正要发怒,陈璞却拉着我的肩膀,说:“算了,别和小孩一般见识。”
这时,突然从街边一座房屋里冲出一个中年女人,披头散发,面色惨白,同样穿着血红的衣裳,她尖叫了一声,一把抱起了刚才袭击我们的那个小孩,转身跑回了屋里。
在街边玩耍的其他孩子,也一哄而散,街道顿时变得清冷起来,一个人也看不到,就如同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般。
我只好无奈地跟着陈璞,沿着一条笔直的青石板马路,穿过了血衣镇,来到一幢老宅前。
这座老宅,与乡村里的寻常宅子相差无几。
一堵不算太高的土墙围绕在宅子外面,黄铜大门紧锁着,两只红色灯笼挂在门庭两侧。
门庭上挂着一张门匾,上面写着四个朱漆掉尽的斑驳大字:书香门第。
陈璞走到门前,大声叫着:“陈卓,开门!陈卓,开门!”
我好奇地问:“陈璞,陈卓是谁啊?”
陈璞漫不经心地答道:“他是我的弟弟,我的孪生弟弟。”
这可真让我感到诧异,以前从来没听说过陈璞有一个孪生弟弟。
我正想多问一句的时候,在我们身后,也就是老宅对面的一幢宅子的门,突然开了。
一个穿着红衣,形容枯槁的老头从屋里走了出来,一看到陈璞,就大声地叫道:“是陈璞呀!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陈璞连忙向我介绍:“这一位,是朱大伯,我家多年的邻居。
我爸生病的时候,全靠他照顾陈卓。”
听了他的话,我不由得有些好奇。
既然陈卓是陈璞的孪生弟弟,现在也应该有三十岁了,为什么还要别人照顾呢?难道他得了什么病?
正当我疑惑的时候,朱大伯开口说道:“陈璞啊,你也有十多年没回过家了吧?刚才要不是我想起才给陈卓喂了刘医生开的药,还以为你是陈卓呢。
你们两兄弟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
”他顿了顿,又说,“陈卓吃过药后,睡着了,你怎么叫他,都叫不醒的。
你家里的钥匙,我这里也有一把。
我去找找,马上给你开门。”
看来,陈璞的弟弟是生病了。
陈璞也跟着朱大伯走进了屋里,而我则无所事事地四处梭巡着。
天已经黑了,朱大伯家门外的灯笼亮了起来。
在昏黄的灯光下,我忽然看到陈璞家围墙的拐角处,站着一个人。
那是一个穿着红色衣裳的女人,头发很长,脸色惨白,暗夜之中,犹如鬼魅一般。
她看到我,什么话都没有说,却缓缓抬起了手,指向陈璞家的围墙。
我顺着她的视线望了过去,看到了一张贴在围墙上的纸片。
纸片是用糨糊贴在墙上的,此刻,纸片下沿的糨糊已经干枯了,随着与夜晚同时到来的寒风,纸片迎风摇曳,似垂死挣扎的白色蝴蝶。
是谁把这张纸片贴在了陈璞家的围墙上?疑惑中,我抬起头,却发现那个鬼魅般的女人竟然消失了,就像她从没有出现过一般。
难道她真是山中的妖魅?传说在深山里,有一种山鬼,长着美女的面容,每当看到生人的时候,全身就会涌出鲜血,浸湿身上的衣裳。
山鬼只有杀死看到的陌生人,才能止住全身流淌的血液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想起了这个诡异的传说。
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,犹如梦游一般,缓慢走到那张纸片前。
我拿出手机,随便按了一个键,手机屏幕闪烁着蓝幽幽的光,恍若一簇鬼火。
在这微弱的光芒下,我看清了纸片上的字迹。
天惶惶,地惶惶,家里有个夜哭郎。
过往君子读一遍,一觉睡到大天光。
在纸片的下方,还画着弯弯曲曲的符咒,符咒下,写了几个字:“姜子牙在此,百无禁忌。山鬼邪灵,速速退散!”
第三章
“王东,你在看什么呢?”身后传来了陈璞的声音,在他的手里,拿着一串明晃晃的钥匙。
我指了指墙上的纸片,声音有点颤抖:“陈璞,这个是什么啊?”
陈璞走近后,瞄了一眼,哑然失笑:“血衣镇离城市太远了,长久以来,一直缺少医疗条件,教育也跟不上。
所以这里的人多少有点迷信,认为小儿夜啼,是受了山鬼的蛊惑。
要想让小孩止住啼哭,就在别人的家门外贴上一张纸片。
如果有过路人无意中看到纸片,并主动念上一遍,喜欢夜哭的小孩就会不再哭泣。
说到底,其实就是种无稽的迷信而已。”
我这才明白了,刚才看到的女人并不是什么鬼魅,而是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。
她的出现,就是想让我看到墙上的纸片而已。
于是我走了过去,对着墙上的纸片,大声念道:“天皇皇,地皇皇,家里有个……”
陈璞推开了老宅的黄铜大门。
门轴已经很久没上过油了,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。
朱大伯领着我们,走进大门。
围墙里,是一个小小的院落,什么植物都没有栽种。
院子里搭了个塑料棚,棚下,摆着两具黑漆漆的棺材。
看到那两具棺木,陈璞并没有露出太多悲伤的表情,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,或许他和父母之间的感情,并没有我想像中那么炽热吧。
走进了黑黢黢的老屋里,朱大伯刚点燃屋里的油灯,我们就听到一阵哭声。
哭声是从里屋里传出来的,“呜呜呜……”,像是孩子在哭泣。
朱大伯皱了皱眉头,说:“大概是陈卓醒来了吧,我去看看他。”
说完后,他借着昏暗的灯光,走进了里屋。
过了一会儿,哭声止住了,接着朱大伯扶着一个穿着红衣、睡眼惺忪的乡村汉子走了出来。
陈卓长得果然很像陈璞,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不过,他的眼神却显得很是呆滞,嘴巴微翕着,黏稠的口水从嘴里淌了出来,挂在嘴边,却不知道去擦一擦。
他看到我们后,嘴里立刻发出了“叽里咕噜”的含糊声音,口水在喉管里打着转,身体也开始兴奋地战栗了起来。
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陈璞从来没给我说过他有个弟弟,原来陈卓是个痴呆症患者。
虽然他长了一副成人的模样,却根本没有成人的思想与感受。
忽然间,不知道为什么,我忽然想起在镇口看到的那几个小孩,他们的眼神,就与现在所看到陈卓的眼神,几乎一模一样。
难道他们也是弱智儿?这血衣镇是怎么了?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智障人士?难道与镇外的那条红色的河有关?
朱大伯在厨房里生了火,为我们打来了热水,还给陈卓熬了药。
他告诉我们,这药是镇里的刘医生给陈卓开的,陈卓吃过之后,很快就会再次睡着。
刘医生是个老中医,在血衣镇里行医已经三十多年了,他的绝活是治疗小儿夜哭症。
只要经他的手,饶是再哭闹的婴孩,也会乖乖安静几天。
不过这几天他外出探亲去了,所以难怪会有妇人在墙外贴着符咒,请求路人的帮助。
陈卓吃完药就进屋歇息去了,我和陈璞烫过脚之后,也进了里屋,躺在了他父母曾经睡过的大木床上。
听着陈卓的鼾声,陈璞幽幽叹了一口气,对我说:“王东,让你见笑了。”
我苦笑:“唉,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”
陈璞告诉我,以前家里很穷,三十年前,当他父亲看到新出生的竟是一对孪生兄弟时,对生活压力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初为人父的喜悦。
三个月后,父亲将陈璞送到了城里一个久未生育的远亲那里,留下了陈卓一个孩子在身边。
这一切是陈璞在十八岁的时候从养父母那里知道的。
当时,养父母认为他已经成年了,应该告诉他所有的真相。
此后,陈璞回来见过父母两三次。
看到这里的贫困与弱智的弟弟后,他决定每个月都寄一笔钱回来。
父母用这些钱,修葺好了这幢老宅,也为陈卓买来了治病的药。
听了陈璞的话,我很有感触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这么多年,真是难为你了。”
第四章
陈璞将油灯放在里屋的桌子上,灯油燃烧后,发出一种很原始的香味。
“睡了吧。”陈璞对我说。
就在这时,我听到屋外飘来了悠悠的哭声。
是婴儿的哭声。
婴儿的哭声像一股烟,在房前屋后飘扬着。
血衣镇里的房屋和树木,将烟一般的哭声切割成一缕一缕的细丝,而哭声却依然会很顽强地重新黏合在一起,水银泻地般,无孔不入地钻进房屋中,刺进我们的耳膜里。
我被这连绵不绝的哭声弄得心烦意乱,不禁对陈璞说:“你听到了吗?有婴儿在哭。”
陈璞翻了个身,淡然地说:“哪是什么哭声?这是山风快速掠过老屋的缝隙时,引起的尖利啸叫。
这样的声音,每天晚上都能听到,你就别担心了。”
油灯光越来越微弱,嗅着那原始的香味,一阵倦意也慢慢袭上了心头。
今天走了这么久的山路,我也真的很累了。
在陈卓与陈璞的鼾声之中,不知不觉,我也慢慢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梦想之中。
朦胧中,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摇曳,仿佛漂浮在水面上一般。
我努力睁开眼睛,却看到周围一片鲜红的液体——原来我正漂在血衣镇外的那条红色的河面上。
我怎么会在这里?我奋力向湖边游去,却呛了几口红色的河水。
河水夹杂着腐烂的恶臭,令我几欲呕吐。
河面上氤氲着紫色的雾,我看不到河岸。
但我知道这小河并不宽,很快我就会游到岸边。
不过,我错了。
河水几乎没有流动,没有一点声息,我根本无法辨别哪里才是河岸所在的方向。
我只能胡乱选择一个方向游了过去,我看到紫色的雾气中,隐隐出现了一座横跨的木桥。
我抓住了木桥的栏杆,挣扎着爬上了木桥。
我湿淋淋地坐在木桥上,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
直到现在,我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浸没在这条恶臭的河里。
就在这个时候,我听到黑暗中,桥的一侧传来脚步声。
我抬头望去,看到了一个穿着红色衣裳的老头,他的面孔隐没在紫色的雾气中。
我只注意到,他的两只裤管,一只捋到了膝盖,而另一只则垂在脚踝处。
垂下头,我忽然看到自己的手里,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。
我的梦境,到此为止。
第五章
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,睁开眼,屋外已是日上三竿,这一觉我睡得可真是香啊。
我坐了起来,才发现自己竟然上身赤裸着。
我记得昨天晚上只是脱掉了外衣,穿着内衣睡的觉。
我有点诧异,这时,陈璞走了进来,他穿上了一件红色的衣裳,对我说:“王东,你醒了?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了,你出了很多汗,贴身的内衣全都湿透了。
你在半梦半醒中脱掉了内衣,光着膀子睡的觉。
”他递给了我一件河水浆洗成红色的粗布内衣,说:“这是陈卓的,你先穿上吧。”
看着这红色的衣裳,我情不自禁想起镇外的那条红色小河,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,一口气憋在胸口,就像塞了一大团浸湿了的棉花。
穿鞋的时候,我发现鞋底全沾染上了红色的泥土。
大概是昨天走了一整天的山路,才把鞋底弄得这么脏吧。
穿上陈卓的衣服,我走出老屋。
现在我才发现,在停放棺木的大棚旁,有一口水井,陈卓正吃力地用摇辘打起一桶水。
虽然这水不是从河里打起来的,但却依然是红色的,红得非常刺眼,就如一桶黏稠的鲜血。
在院落一侧,晾着我的内衣,此刻已经变成通红一片,挂在绳索上,就如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无头士兵。
陈璞对我说:“按照乡村里的习俗,今天我要在院子里摆上席桌,请全血衣镇的人吃一顿饭——这就是所谓的白喜。
然后明天将两具棺材送到殡仪馆,火花后带回血衣镇,埋在镇外山坡中的祖坟里。”
过了一会儿,朱大伯带着几个来帮手的乡亲,来到了老宅的院落里,架起几口锅,在空地上摆了一排桌子。
朱大伯对我们说:“一会儿罗婶来了,就可以开始做饭了。
罗婶是远近闻名的巧手厨师。”
陈璞问:“罗婶去哪里了?”
朱大伯说:“我来的时候,正好看到她抱着孩子去刘医生那里去了。
这几天刘医生不在,她家的孩子老是哭个没停,夜哭症又犯了。”
他刚说完,院子外就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:“不好了!救命啊!”陈璞家的大门是开着的,一个身着红衣的女人冲进了院子里,一头栽在地上,身体不停抽搐着。
我一眼就认了出来,她就是昨天夜里在围墙上贴符咒的那个女人。
朱大伯和另外几个乡亲扶起这个女人,朱大伯问:“罗婶,你这是怎么了。”原来,这个女人就是罗婶。
罗婶深深吸了一口气,高耸的胸脯起伏了好几下,才一字一顿地说:“刘医生,死了。是被杀的。”
说完这几个字,她就忍不住继续尖叫了起来:“啊……天哪,我的儿子还放在刘医生的屋里,和死人呆在一起!”
她歇斯底里地冲出了院子,朝镇尾飞奔而去。
我们跟在了罗婶身后,赶到了镇尾的刘医生诊所。
诊所的门开着,还没进去,就听到里面传来婴儿的哭声。
走进屋里,刘医生的尸体躺在地上,胸口全都是血,红色的鲜血与同样鲜红的衣服混在一起,显得格外妖艳。
婴儿的摇篮就摆在尸体旁,婴儿一边大声哭泣,一边睁大了眼睛,望着走近的这群陌生人。
初生的婴儿与死去的老人并排在一处,真是一副极端诡异并且充满了哲学意义的场景。
我挤进人群,终于看到了刘医生的尸体。
接着,我感觉到一阵眩晕。
因为我看到了刘医生的裤管,一只捋到了膝盖处,另一只则垂到脚踝,正与我昨天夜里噩梦中看到的那个老人一模一样!
而刘医生诊所外的泥土,则是红色的,红得像鲜血一样。
第六章
我都不知道是怎样跟着陈璞他们浑浑噩噩地回到了老宅里。
朱大伯报了警,可这里距离最近的警署,也有足足一天行程,要到明天上午警察才会赶来。
刘医生的诊所被封锁了起来,镇上的居民都来到了陈璞家。
席桌一直摆到了街上,罗婶吃过了朱大伯找来的药后,也恢复了很多,亲自下厨炒起了菜。
她的手艺真的很不错,尽管只是一些山村里的普通菜肴,但在经过了她的手之后,就变得色香味美俱全,活色生香。
尽管镇尾还停放着一具刚被谋杀的尸体,但居民们却还是依然开心地觥筹交盏,相互劝酒。
或许在他们看来,别人的死活并不重要,只要能喝到不要钱的酒,哪怕天塌下来了也没关系。
不过,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
我的脑海里,老是浮现着刘医生的那两只裤管,一只高,一只低的裤管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梦中见到的一个老人,竟会真实存在,而且还成了一具尸体。
我想喝口酒,但血衣镇里的酒,都是用镇外那条河里的河水酿成的,不仅有股淡淡的腥臭,而且颜色还是红的,红得像鲜血一样,这让我更加没有食欲了。
我垂下头,看到了鞋底上沾染的红色泥土,这更让我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心悸。
幸好,我并不是这场宴会中唯一失落者。
在院落里,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没有食欲的人。
陈璞的弟弟陈卓,带着一帮镇里的小孩,根本不理会大人的呵斥,只管在棺木旁的井边,玩着纸牌游戏。
陈卓和这些小孩的眼神几乎完全一样,都是那种毫无光泽、毫无神采的眼神。
而他们那迟缓的动作,与不时的傻笑,更是验证了他们都是智障者。
如果是镇外那条红色河的水源被污染了,才造成了这些智障者的产生,那为什么只有小孩变成了智障,而大人却没事?要知道,陈璞曾经给我说过,这条河已经流淌了几百年的红色河水了。
宴席上,镇民们喝醉了便就地躺下,睡醒后又继续喝。
整个院落里,到处都是散发着酒味的呕吐物。
宴会没有停顿,晚饭和午饭连接在了一起,罗婶一直都在锅灶边忙碌着,婴儿绑在她的背后,不时大声哭闹着,这也让她不敢有丝毫的放松。
我走到罗婶身边,说帮她抱抱婴儿,她却拒绝了。
我问她:“听说刘医生有治疗婴儿夜哭的秘方,你们在诊所里没找一下那个药吗?”
罗婶皱着眉头说:“刚才我们在诊所里找了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却一瓶药水都没找到……”
这时,陈卓提着一桶红色的井水走了过来,递给罗婶,语音含糊地说,这水是他哥哥让送来的。
该煮晚饭了。
罗婶舀起一瓢红色的水,倒进了刚淘好的米里。
晚饭的时候,陈璞不停到每一桌去敬酒,满脸通红,幸好镇里自酿的米酒度数并不高,所以看上去他还没有不胜酒力的迹象。
不过,米酒的后劲很足,当夜幕降临,大家吃完米饭,酒席快要散尽的时候,陈璞终于受不了了。
他在我的搀扶下,进屋刚点上油灯,就一头倒在在床上,睡着了。
等我再走出屋的时候,酒席上一片狼藉,席桌边上,镇上的居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,他们都喝醉了。
酒席上常常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,只要有一个人喝醉,其他人也会跟着醉。
读大学的时候,教我们心理学的老师曾经说过,这是一种叫做群体无意识的反应使然。
其实,这是伟大哲学家荣格的理论。
回到里屋,我看到陈卓也躺在床上,从他的裤兜里,露出了半个盒子,是一盒药。
我走到他身边,掏出了这盒药,看了一眼,又放回了他的裤兜里。
走到床边,我将油灯拨得更亮了,豆油燃烧发出的香味,钻进我的鼻孔,这让我感觉非常舒服。
忽然,我听到陈璞翻了个身,然后打了个哈欠。
我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,一阵无可抵挡的倦意袭上了心头,打哈欠也是会传染的,这也是荣格群体无意识理论的一种体现。
我脱掉沾满红色泥土的鞋子,躺在床上,四肢舒畅地摊开,闭上了眼睛,等待睡魔的再次降临。
第七章
等我悠悠醒转过来的时候,闻到了一股很浓重的血腥气息。
油灯的灯光摇曳着,我睁开眼睛,看到土墙墙壁上,我的影子被拉得一会儿长,一会儿短。
这时,我听到一声幽幽的叹息,是陈璞的声音。
他坐在我的对面,抽着烟,落寞地望着我。
我想坐起来,却发现在我的手里,似乎拿着什么东西,抬起手,我看到了一把锋利的匕首,正握在我的手里。
刃口上,还滴淌着来历不明的鲜红液体。
我再向身边望了一眼,顿时张大了嘴,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陈卓躺在我的身边,胸口正冒出鲜血,将他那红色的衣服,浸得更加鲜艳。
他的胸口上全是匕首造成的伤口,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我的手上,满是陈卓的鲜血,在他的衣裳上,也到处是我的手掌印。
究竟发生了什么?我忽然感觉到一阵眩晕,天旋地转!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我颓丧地问道。
陈璞叹了一口气,说:“半夜的时候,我醒了过来,想喝杯水,就看到了你手持匕首,躺在陈卓的身边。我猜是你在梦游的时候,杀死了陈卓。”
“梦游?瞎说!我从来没有梦游过!”我叫了起来。
陈璞不紧不慢地说:“王东,我来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,这故事发生在前一个夜晚。”
第八章
昨天夜里,陈璞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忽然尿急,他起身后,却发现我不见了。
他走出老屋,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——是我。
是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内衣,眼睛闭着,颈脖僵硬,手里拿着一把匕首,缓慢走出了老宅大门。
陈璞跟着我,走出了老宅。
他看到我走出了镇口,踌躇在红色的小河旁,忽然间,我跳进了河里,穿着鞋,穿着内衣,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。
我在河里漂浮着,游到了木桥边,然后沿着木桥的栏杆,攀上了桥面。
陈璞连忙绕着河岸,走上了木桥。
这时,他看到了骇人的一幕,我跪在桥面上,手里拿着匕首。
在我的身前,躺着一个穿着红衣的老人,是刘医生,我正举起匕首,一刀一刀扎进刘医生的胸口。
可怜的刘医生,连句临死前的呻吟都没发得出,就已经断气了。
我杀死了刘医生后,站了起来,转过了身,眼睛依然闭着。
我继续缓慢地行走,从目瞪口呆的陈璞身边经过,却仿佛没有看到他,径直向老宅走去,消失在了紫色的雾气之中,只在桥面上留下了一具老人的尸体。
陈璞知道,是我在梦游里杀死了刘医生。
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所以不愿意让这一切被镇里的居民知道,他想要保护我!陈璞抱起刘医生的尸体,快步穿过血衣镇,来到镇尾刘医生的诊所里。
他将刘医生的尸体扔在了诊所中,才发现自己的外衣上,全是刘医生的血。
而脚上,也全是红色的泥土。
回到老宅后,他立刻脱下了外衣,在井里打了一桶水。
将血衣扔进水里,很快红色的井水就与血液融合在一起,看不出一点鲜血的痕迹。
进了屋,陈璞看到躺在床上的我,身上的内衣也全是鲜血,于是他也帮我脱了下来,扔进了桶里。
我也睡得真死,竟然连衣服被人脱下来了都不知道。
故事讲完了,我目瞪口呆。
垂下眼帘,我悲伤地问:“陈璞,你说的都是真的吗?”
陈璞点了点头,说:“王东,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?”他走到我身边,说,“你放心好了,你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会永远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
我和陈卓没有任何感情,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的生死。
今天的宴席里,大家都喝醉了,我会告诉所有人,你也一样喝醉了,当我醒来的时候,你还依然沉睡着。
镇里的人会以为凶手另有其人,或许他们还会以为凶手就是杀死刘医生的那个人。”
我无力地握着匕首,说不出一句话来,我几乎不能将凌乱的思维有效地组合在一起。
看着陈璞,忽然间,我举起了匕首,一刀扎在了陈璞的大腿上。
陈璞一声尖叫,捂着大腿在地上打滚。
他的额头冒着大颗的汗液,大声问我:“王东,你这是在干什么?”
我笑了笑,说:“陈璞,我也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第九章
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夜里。
没有过多久,陈璞就醒了过来。
他起来后,看了看一旁的我,探了一下鼻息,证实我依然熟睡着。
然后他拿出了匕首,握在手中,走到了陈卓的床边。
陈卓睡着的时候,嘴里还滴答着黏稠的口水。
陈璞冷笑了一声,将匕首插进了他的孪生弟弟的胸膛里,一刀,然后又是一刀。
等他确定陈卓已经死亡后,他把熟睡的我搬上了陈卓的床上,把匕首放在了我的手里,然后点上一根烟,静静地等待着我的醒来。
屋里的油灯,在燃烧时会发出奇怪而又原始的香味,那是因为在油灯的豆油里,掺进了曼陀罗的粉末,那是一种可以让人快速昏迷的药物。
不用说,刘医生也是陈璞杀的,他编出那套谎言,就是为了让我相信,是我杀了刘医生。
或许,在他邀请我来血衣镇的时候,就决定了要嫁祸给我。
“王东,你胡说,我没有做这些事!我发誓!”陈璞叫了起来。
我没有理会他,继续说:“知道我是从你的那句话里,找出破绽来的吗?”陈璞的声音陡然停止了,大概他也想知道自己在哪里做错了吧。
我说:“在你的那个故事里,我是在桥上杀死了刘医生,然后你把刘医生扛回了诊所里。
在这里就有个漏洞,刘医生诊所外的泥土是红的,而我的鞋底也沾满了红色的泥土,可是在你的故事里,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刘医生的诊所!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,是你穿着我的鞋子,去诊所杀死了刘医生。
你在现场留下了我的脚印,就是想让村民们发现,以为我是凶手。”
陈璞的脸上一片惨白。
他歇斯底里地叫道:“你瞎说,我刚刚才醒来,今天我喝了这么多酒,哪有什么精力来做这些事?你所说的,全是无稽的假话!”
我笑了一下,说:“其实,我有证据的。”
我扒拉了一下陈卓的尸体,从他的裤兜里摸出了一盒药。
这是一盒知名厂家出产的解酒药,据说每次饮酒前服用两粒,就会让酒量翻上一番。
陈卓这么一个痴呆症患者,是弄不来解酒药的,只有一个解释,他偷偷在陈璞那里拿来的。
这一下,陈璞说不出一句话了。
而我则继续说:“既然你能嫁祸我杀了刘医生,自然也可以嫁祸我杀了你弟弟。
我还可以推理出你杀陈卓的动机,是为了减少负担。
你的父母死了后,照顾弟弟的重担顺理成章就落到了你的身上。
不过,我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了刘医生,你已经十年没回过血衣镇了,我真猜不出你有什么动机要杀刘医生。”
陈璞木然地望了我一眼,说:“王东,或许我真的不该带你来血衣镇。好吧,让我再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第十章
“王东,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孪生弟弟陈卓会变成痴呆症患者吗?你知道为什么血衣镇上有那么多的智障儿童吗?你知道刘医生是用什么方法治疗小儿夜哭吗?
一个月前,血衣镇的罗婶给我寄了一封信,说刘医生探亲去了,她拿不到刘医生给儿子开的治疗夜哭症的药。
只好用符咒的方法来医治儿子的夜哭症,可一点效果也没有。
于是她把药水寄给了我,托我帮她在城里买瓶一样的药。
血衣镇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城里,常常让我帮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忙。
可是,她寄来的药,是刘医生自己配制的,不是成药。
我只好送到了一个做药物分析的朋友那里,让他帮我分析一下药物里的成分。
结果很快就出来了,朋友告诉我,药水里最重要的成分是*。
这是一种强力的安眠药,比普通的安定效果好了近百倍。
刘医生就是用*溶液来治疗小儿夜哭症。
吃了这药水后,婴儿自然就睡着了,哪里还会哭?
于是我问做药物分析的朋友,如果婴儿吃了这样的药水,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
朋友告诉我,婴儿服用过量*溶液后,会出现神经系统的紊乱,长期服用,更会造成焦虑、痉挛,甚至可怕的痴呆症。
在这个时候,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孪生弟弟会变成痴呆症患者了,也明白了为什么血衣镇上会有那么多智障儿童。
于是我决定要替天行道,杀死刘医生这个该死的庸医。
而杀死陈卓的原因,正如你所说的那样,我的生父母去世后,照顾陈卓的担子压到了我的身上。
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,我可不想让一个痴呆的弟弟束缚住我的生活,所以我必须杀死他!
至于为什么我要带你来血衣镇?呵呵,我设计的谋杀手法天衣无缝,绝对不会有任何破绽。
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,你会在我的设计下,认为是我救了你,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更进一步。
对了,我没告诉过你吧?其实,我不喜欢女人,我一直认为,你和我很般配的……”
听完了陈璞的故事,我狠狠冲他腰间踢了一脚。
看他在地上挣扎着,我对他说:“陈璞,按照你设计的阴谋,根本不是想让我对你感恩,而是想胁迫我。
你想一想,如果现在有血衣镇上的居民走进了这间屋里,看到这里的情形,他们是相信你设计的谎言,还是相信我的话?难怪你会穿着我的鞋子去杀刘医生,你是在制造铁证!要知道,明天警察就来了。”
陈璞的瞳孔骤然收缩,他看到我举起了手里的匕首,浑身战栗地问:“王东,你想干什么?”
我笑了笑,说:“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要做什么。我只会告诉你,我最后要干什么。”
在做完了眼前要做的这件事后,我会脱下身上的血衣,扔进井水里。
鲜血会与红色的井水融合在一起,不留一点痕迹。
对了,我还会去吃一碗饭。
做晚饭的时候,陈卓送来的那桶水被加进了*,所以那些居民们才在吃完饭后全晕倒了。
而*是陈璞在昨天夜里杀死刘医生后,在诊所里拿走的,难怪罗婶在诊所里连一瓶药水都找不到。
只要我吃了一碗*溶液煮成的饭,在我的体内就会存在药物的残余。
这样,我也可以向警方解释,吃完晚饭后我就睡着了,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屋里会有两具尸体——陈卓与陈璞的尸体!
最后,我要对陈璞说,对不起,我这么做,全是被你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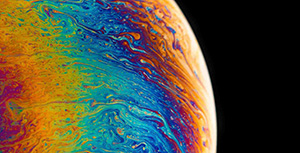

-d2979772834f4346a961b123d2a49447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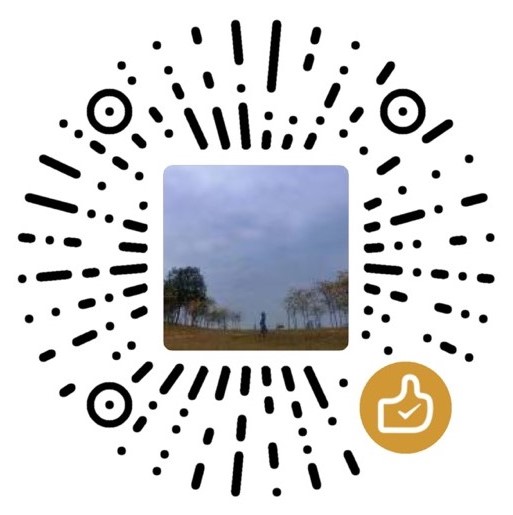

评论区